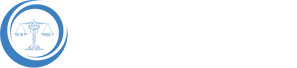文章分類
從黃國昌狗仔疑案看澳洲、台灣跟拍的法律界線(上集)

- 2025-10-04
- 2025-10-04
- 484 Views
- 楊芷沁
從黃國昌狗仔疑案看澳洲、台灣跟拍的法律界線(上集)
台灣近日沸沸揚揚在各媒體與社群平台熱議「黃國昌是否組織狗仔長期跟拍政界人士」,從租用住家車位監看、到連續多日尾隨,相關指控把「監督公眾人物(Public Figures)」與「侵犯他人隱私」的界線,再次推到聚光燈下。新聞報導指稱,遭長期「跟拍」者包括多位政治人物;也有人質疑這樣的「監看工程」經費來源與正當性。
一、《刑法》
這裡所謂的「跟」,意指跟蹤、跟監(Stalking, 盯梢他人),而「拍」,乃指拍照、拍攝(Photographing)等。就台灣《刑法》而言,可能觸犯刑法第315條之1規定:「有左列行為之一者,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:一、無故利用工具、設備窺視、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或談話者。二、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或談話者。」評價關鍵在「地點性質」與「取得手段」,而所謂非公開,是指個人主觀上不願讓人知悉,且客觀上依社會通念也認為此隱私應受保護的範圍。若於非公開空間(如住居所、管制停車場)以器械窺視、錄音錄影,他人之非公開活動、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,即可能觸犯妨害秘密罪;即便未散布,也已成立。
二、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
就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觀之,未經當事人同意而拍攝足以直接辨識身分之影像(如清晰可辨之臉部),原則上即屬蒐集「個人資料」。非公務機關如欲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該等資料,須符合第19條與第20條第1項所定之合法性基礎,包括:取得當事人同意、法律明文規定、為履行契約所必要、或基於特定目的且不逾必要範圍等。倘若行為人既未取得合法授權或有效同意,亦未能證明其行為符合前開條文所許之正當事由與「特定目的、必要範圍」之限制,即屬違反個資法之蒐集/處理/利用規範。如其行為符合第41條所規範之構成要件(例如以不法意圖而違法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,並致生損害等),即有成立第41條所定「非法蒐集或非法利用個人資料」等犯罪之可能。
三、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
此外,還可能違反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第83條第1款規定:「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,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罰鍰:故意窺視他人臥室、浴室、廁所、更衣室,足以妨害其隱私者」。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:「無正當理由,跟追他人,經勸阻不聽者,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」。
公眾人物仍應享有其私人生活(個人隱私)。「公益」不是免死金牌,監督者不能也不可以此為由,取得並使用這些自其私領域取得的影像(即或這些資料具新聞價值),仍會觸犯刑事、個資與社維法責任;若存在教唆指揮,教唆者亦將依所教唆之罪負同等刑責。
「本文內容僅供大眾作為法律常識,不代表本所或律師之法律意見 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」— 澳華國際法律事務所法務助理 楊芷沁 撰文 / 陳律師 審訂
參考資料:
全國法規資料庫
圖片來源:iStock